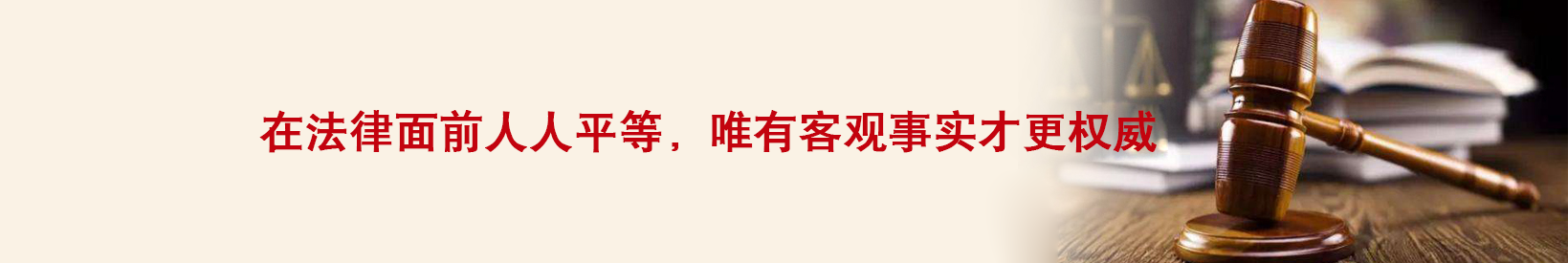关于电影《1942》的分析
冯小刚导演的电影《1942》讲的是发生在中国河南70年前的一场大饥荒给人民带来的苦难。电影将河南一户大地主家置于这场大饥荒的漩涡中心,通过他们一家人和乡亲们逃荒的故事,把一个个血淋淋的伤疤揭开,却仍然困惑苦难的根源,苦难是与幸福相对的一个词组,而苦难的经历撕裂了许多常态生活下人们触及不到的许多问题。在笔者看来,电影通过饥饿的苦难拷问了人类生存的局限,包括生死局限、信仰局限、伦理局限、政治局限、求真局限等方面。

一、生死局限
故事往往以冲突和抗争为主线,《1942》也不例外。这次与命运冲突的是河南农民,他们因为大旱而面临饿死的威胁,为此进行了远途流亡,途中遭遇到粮食短缺、溃兵抢夺、日寇屠杀种种灾难。在与灾难的抗争中,农民们一个个都失败了,留给我们无尽的思索。
人类历史表明自远古时起人就有长生不老的诉求,《圣经》中伊甸园里居住的人类始祖原本也是可以长生不老的、无忧无虑;古巴比伦有《吉尔伽美什》中同名主人公求取不死草的故事;《西游记》中不仅有不死的神仙,还有可以延年益寿的仙丹灵药,更有可使凡人长生的稀世仙果人参果。然而人的生命毕竟是有限的,无论是居庙堂之高的大人,还是处江湖之远的草民,终归会驾鹤西去,撒手人寰,这是人类的局限,也是生命哲学中不可逃避的重要问题。似乎人们都能平静接受生老病死这一无法改变的事实,然而人的苦难却是那无可预测的硬生生打断生命进程的天灾人祸。
影片开始,镜头展示1942年的大旱给延津县人民带来的苦难,一群饥肠辘辘的灾民,正围攻有一户囤积少许粮食大地主的村寨。本村人与外村人在对峙后发生了武斗,少东家在混战中被杀,大户宅院被烧,老东家带着家眷,同延津县的灾民一起,开始了为逃避饥饿威胁的流亡。这一路颠簸劳顿,使本是富贵中长大的地主家人叫苦不迭,但这突发的灾难中断了原本动物性繁衍生存的村民的生活。笔者定义这是动物性生存,不是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指责或启蒙,而是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词语来描述那种机械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只为繁衍后代的生活。
老东家及其长工还有同村的农民一起逃荒,大家共同面对了饥饿带来的死亡威胁。随着流亡时间的延展,离家的距离也越来越远,身边的粮食却越来越少。最先遭遇到饿死威胁的是以瞎鹿为代表的普通民众,眼看着所带的最后一粒小米吃尽。大雪飘飞的寒冬中,瞎鹿的老母亲首先扛不住了,寒冷的腊月发高烧,终于带着不能埋葬在老家的遗憾离开了人世。老东家尽管也是灾民,但毕竟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细软和粮食装满一马车。有粮食流亡似乎不是逃荒,老东家一家开始也一直强调自己是逃难,这个难笔者认为是两层意思,一是普遍的旱灾之难,二是被打劫之难。人世间不测风云不仅来自上天,更有来自人类的贪婪与暴虐。逃亡路上遭遇到溃兵和日本飞机轰炸那一刻十分惨烈,眼看着屏幕上战斗机呼啸着把炮弹投向混杂着溃兵的逃荒队伍,血肉横飞,人仰马翻,因为日本兵的炸弹,无数人在向往着异乡有吃食的寻梦路上死亡。异族人的枪炮过后则是本国溃兵的二次掠夺,老东家的细软和粮食也眼睁睁地看着被溃兵用枪杆子威胁着带走。粮食欠缺而带来的饥饿让生死问题再次严峻起来,这种严峻比威力无比的枪炮带来的痛苦还要惨烈。人一点点被抽掉力气,一点点地失去生命机能。老弱病残成为第一批在这大灾之年的丛林法则中被淘汰的人,然后就是壮年人为争取活下来而展开的生存竞斗,人彻底沦落为动物性的人。
二、价值观危机
西方心理学家马斯洛认为,人的需求是分层次的,由低到高。它们是: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实现需求。而人类最基本的需求是生理需求,吃喝拉撒睡如不满足会有生命危险。当人的最低层次需求无法保障时,文明时期构建的伦理藩篱就会被打破。饥饿的威胁使得人渐渐丧失羞耻感,为了减少粮食消耗瞎鹿竟然要卖孩子;为了吃块饼干星星也自愿亲吻长工栓柱,而花枝则说出“给我饼干,我给你睡”。直到最后洛阳城下,为了糊口,老东家眼睁睁地看着星星以5升小米被人贩子买走,再被卖进青楼走上不归路。而这一切都是为了暂时能吃上饭,能活下来。千百年维持社会良性运转的伦理观念在饥饿面前坍塌,那么更高一层次的宗教信仰能否引领人们走向光明和宁静呢?
信仰和苦难也是一对形影不离的名词,往往是苦难的人在无可奈何的状态下会求助于拥有超能力的神灵,希望通过自己的信仰和供奉神灵而得到庇佑,进而使人生走向凡人追求的幸福和谐的状态中。
影片有多处刻画基督教神父形象的场面和镜头,一是中国神父安西满,一是外国神父梅干。前者是土生土长的河南农民,怀着对基督的赤诚信仰为自己的老乡传教,希望在灾荒中的民众坚强地生活,更希望他们能够皈依基督而不再迷惘。后者是意大利天主教牧师,他在中国生活30多年,对中国现实和宗教教义均熟悉。两人背负着为其信奉的天主传播福音的神圣使命,并以坚毅的品行履行自己的职责。小安神父随着灾民传教,在老东家被所谓的“贼人”抢烧后,他即出现在收拾残局的人群中,用烧焦的一长一短的木头做成一个十字架,向民众呼告着信奉上帝以承受恩泽。虽然饥饿的民众无暇听他的演讲,安神父依然信心满满地传播宗教教义。在逃难路上,一大户客死途中,严寒和饥饿使亡者的尸体冻僵,人虽死,眼未闭。按照中原农民的理解这叫死不瞑目,以为亡者还有心事未了。安神父主动要求为亡者做弥赛,并邀请瞎鹿拉弦子,瞎鹿以饿得没劲拒绝,安神父从自己的干粮袋中拿饼子给瞎鹿做酬劳才说动后者参与做弥撒。可是他的一番充满宗教意义的唱词未能使亡者闭目,伴着遗憾和疑惑的安神父只好让死者下葬。在宗教福音的召唤下仍然死不瞑目,象征着苦难的痛楚深入骨髓,难以依靠意念中的天国慰藉伤痕累累的肉体。 安神父依然不离不弃,当灾民在日本战斗机轰炸中大面积死亡时,他坚持以宗教人道主义救助伤者和亡灵。值得深思的是,正当他虔诚地将《圣经》按着流血的枪眼做弥撒时,一颗炮弹落下,若不是有人及时将他推开,他的肉体也会升入其信念的天国。随后,屏幕上落下大片大片的纸片,传承几千年宗教经典《圣经》被现代化武器炸成了零散的书页。导演这样处理《圣经》被炸笔者解读到两点意思:首先是对宣扬宽容的宗教能否终止苦难和暴虐的怀疑;其次是《圣经》虽然被炸散了,却没有成碎片,而是一页页地散开,象征着信仰依然有力量,但必须以另一种方式聚合在一起。
安神父冒风雪来到梅干神父的教堂,包扎好伤口后他不解地问梅干关于灾民的苦难:“上帝知道吗?”这不仅是一个信仰者的疑问,也是所有善良民众的疑问。梅干神父则把苦难的根源推给了魔鬼:“是魔鬼引起的。”我们很容易联想到《圣经?约伯记》中义人约伯无辜受难的故事来,仅仅是上帝与魔鬼的一个赌赛。魔鬼要把义人引向怀疑上帝乃至反对上帝的虚无主义道路上去,而上帝则坚信人的信仰终能使其得救而不误入歧途。魔鬼怀疑人敬畏上帝是因为人是上帝庇护的受益者,如若上帝疏离人类,人类则必将抛弃上帝而另选为其赐福的超人类力量来供奉。也就是说:“‘利益’一旦长久地缺失,常态一旦被极端事件所打破,建立在‘利益’基础之上的信心必然会随之瓦解。”①
三、灾难成因
电影毫无疑问是在讲述一场悲剧,而鲁迅先生说“悲剧是将有价值的东西撕毁给人看”。正是因为悲剧撕毁的是有价值的东西,才令人扼腕、令人震惊。那么1942年这场灾难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威力呢?灾难的成因无疑是电影意图探讨的另一个问题,这条线索是通过美国记者白修德坚持求真的敬业精神和不畏死亡威胁深入灾区实地调查而完成的。我们常说真善美是社会的主旋律,是人类普遍追求的永恒价值。但是电影中人们对河南大旱灾难的真实情况的了解却是那么艰难。
灾难成因多种多样,天灾之外还有人祸,所谓天灾就是大旱致使田地绝收,粮食生产中断。所谓人祸,首要表现为政府不作为。官僚主义作风和一贯傲慢的姿态注定底层民众的苦难不能进入政治精英的视野,不是不能而是不愿。这才有了河南省主席到灾区不是赈灾而是催粮,河南省主席到重庆反映情况却被种种“重大的”外交事件巧妙地搪塞,《大公报》将灾难的部分真实情况如实报道却受到休刊整顿的惩罚。无政府状态下的危机中,人群中奉行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掌握枪杆子的军队肆意要挟政府,不顾灾情征收军粮;大兵任意征用灾民器物钱财;老东家和长工抢劫外国记者。
其次,灾难加剧源于政府官员腐败成风。面对灾情,影片中的各级国民政府、各个部门均从自身小团体利益出发,不但不去思考如何救灾,反而想方设法捞取发财的机会。县长去省政府要救济,军队要省政府出军粮。鲜有体恤民情的官员为民请命者,省政府主席李培基表面上一本正经要为老百姓争取救济。到了重庆要员面前却欲言又止,硬说“河南能克服”。等到白修德的报道被《时代周刊》发表,引起世界哗然之后,各级政府为了在友邦面前的面子才不得已调集粮食救灾。面对即将划拨的8千万斤粮食,各行政部门又以自己部门特殊为由争取利益最大化。而拥有枪杆子的军队却强行夺取救灾粮,然后军需官又与奸商勾结高价出售救灾粮。
灾难加剧的第三个原因是军纪涣散。当时抗日战争正打得如火如荼,日本帝国主义对河南的攻势日炽。溃退的国军与逃亡的灾民混在一起,日帝轰战机不分青红皂白,不论军民一起轰炸。外敌肆虐后,国军的残兵称霸王,在灾民中予取予求、胡作非为,欺男霸女,抢夺民财。更讽刺的是一个厨子领两个团练组成的维持正义和公道的巡回法庭也大言不惭,名里调解治安,实则巧取豪夺以中饱私囊。老东家的长工栓柱因持枪而被这个所谓的法庭拘捕受审,老东家无奈只得以3升白面换人,赖以防卫的长枪却被没收。
到这里笔者不禁想起《孟子》里的夫子对梁惠王的一段话:“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涂有饿莩而不知发;人死,则曰:‘非我也,岁也。’是何异于刺人而杀之,曰:‘非我也,兵也。’王无罪岁,斯天下之民至焉。”②为政者临危机当局其所,成为民众面临苦难的支柱,而不能不管不顾还将责任推卸给天灾。
四、结 语
对苦难及其缘由的追问是人生中的难题,也是宗教和哲学不可回避的难题。对于痛苦的经验,不同人有不同的反应:或否认、避而不谈;或认作宿命而匍匐在命运脚下;或在“及时行乐”思想的指导下追求物质欲望而忘却人的精神实质。1942年的河南旱灾已经凝结成人类苦难的经验沉淀在记忆中。后人的追问使得这符号化的事件成了反思人的存在、人的信仰、人的价值时无法逾越的障碍。对苦难的反思,特别是人祸的反思必然会涉及道德和人性裂变带来的剧痛,但这是苦难经验给后人留下的反思空间,促使后人力促那些错位的各种观念回到理性而人道的正途上来,正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