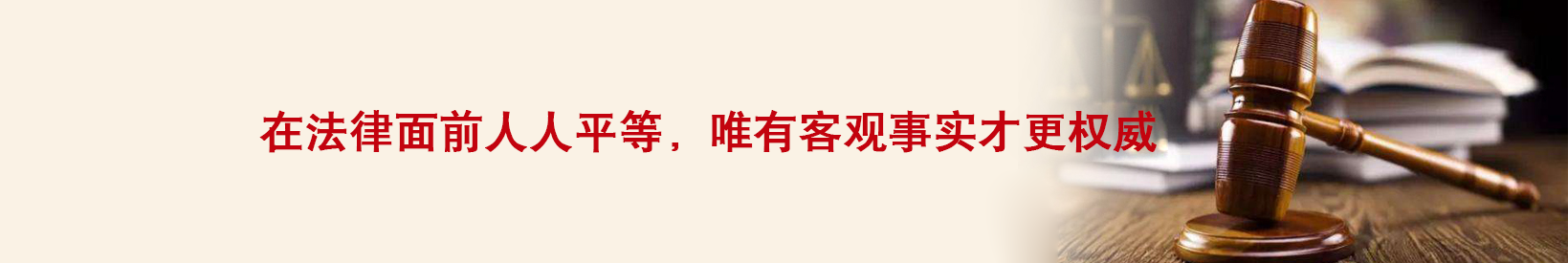话剧《二月》:一次庸俗化的失败改编 ——致李六乙导演的一封公开信

李六乙导演:
写这封信并非我的本意。我的初衷原本是想评论一下您的新作《二月》,但动笔后总觉思绪难平,很想跟您敞开心扉聊一聊,遂决定改成书信体,以普通观众的身份,斗胆说一说对您作品的感受。我此前看过您的一些戏剧作品,还曾撰文写过评论文章,但我不敢说对您的创作有多么深刻的了解,但接下来的字字句句都是肺腑之言,如果言语中有冒犯之处,还望您能够原谅。
自从得知您要把柔石的小说改编成话剧,我便对此十分关注,因为您对媒体所说的一句话深深地打动了我。您说:“这是一部90年前的作品,但我们把它做成一个当代作品创作……它关乎当下,无疑也关乎未来。”我当初读小说时,也是隐约从中感受到了“当下”和“未来”的,于是很想见识一下您打算如何表达此番体悟,看一看90年前的文本如何在“当下”这个“未来”生发出新的意义。
站在二十世纪初叶的柔石,在小说中借人物之口说:“我想我自己是做世纪末的人”;他似乎还为后来的演绎者回望自己所处的时代提供了很好的理由,因为“每当未来底(注:原文写作‘底’)进行不顺利的时候就容易想起过去。”我想当然地以为,这几乎应该是今天的创作者改编《二月》这部小说的唯一出发点。但是,当我看完这部长约三个小时的话剧后,却产生了彻底的怀疑和失望。
我既没有看到您所宣称的“当下”和“未来”,也没有看出这所谓“人文戏剧的艺术实践”创造出了什么新鲜的美学价值。我看到的只是满台捧着原著借尸还魂般的人物在装腔作势,如果硬要说有什么况味,大概就是无聊罢了。请您不要误会,我所说的无聊,并非鲁迅当年评点小说《二月》中那些人物时所说的“无聊”,毕竟小说中的无聊还是颇值得思忖的,而您的戏剧实在叫观众看得无聊。
近年来国内的戏剧演出环境蓬勃,但真正有艺术水准的作品寥寥。不太成功的戏总有各自不同的毛病。我看他人的戏,要么是技术层面存在硬伤,要么是表达层面不够深入;但您这戏却与旁的戏不同,思前想后琢磨了许久,问题似乎是出在您的创作意识和美学观念上,犯下的是一些独树一帜的错误。因此,这封信虽然以公开发表的形式递到您面前,但确实是只针对您个人的创作而言的。
舞台“奇观”如何成全艺术的野心?
我以个人对戏剧创作的浅薄认知揣测,将《二月》改编成话剧似乎本不应该有什么难处,因为毕竟有柔石的原著打底。如果这次创作对您而言并不是命题作文,那么我想您一定是认同原著的文学水平的,也一定是看到这个作品有着极好的改编基础的。我以为,柔石原著的好处,便是鲁迅当年为这篇小说做引文时所说的“工妙”二字。
小说中,青年知识分子萧涧秋来到芙蓉镇教书,与女青年陶岚互生爱慕之情,又因救助烈士遗孀文嫂而被卷入流言蜚语,最终不得不离开这个是非之地。整部作品叙事流畅,情节紧凑,冲突明晰,场景集中,描写细腻,大量穿插萧涧秋与陶岚的往来书信,完整剖析了主人公的心理活动,为后来的改编者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当年电影《早春二月》所以成功,便胜在忠实地化用了原著中的这些长处。

电影《早春二月》
但是,您大概是不甘心或者说不屑于以如此老实的态度来进行创作的。一来您似乎有着很大的艺术野心,不仅早早便自贴上“纯粹戏剧”的标签,近年的作品中更是常常展露出一些令人费解的意念,并且自认这是“回归戏剧的本来”;二来您这次背靠国家大剧院,大约是不怎么差钱的,于是可以不惜成本地在舞台上砍伐出许许多多的“奇观”出来。
比如,您把舞台改造成了倾斜角度颇有些惊悚的铁皮坡面,还在上面开凿了一些或深或浅的孔洞,升起几把东倒西歪的椅子,又把舞台前面“挖”成一片深渊,戳进几根长短不一的石柱,并且在演出中呼风唤雨般地下了好几场雨雪。但是恕我直言,我在观演过程中始终无法感受到您所营造的意境和美感,因为每当演员在这样的舞台上腾转挪移,我都会因为生怕他们掉进您挖的洞里而提心吊胆。
您对您的演员是否也会有如此的关切之情呢?我想不会,因为您连您的男一号都不怎么照顾,甚至连他的形象都没有找人好好打理一下,竟然允许他梳着“拖到颈后”的长发就登台了。您照搬了小说中的台词,应该知道萧涧秋登场前本就该剪去这长发了吧?还是说这都是您故意而为之的安排?难道说您选择这位男演员,只是相中了他弹钢琴的技艺?所以让他长时间背对观众,生怕露出眉眼。
“不说人话”的表演便是高级的艺术?
对于原著的文本,您倒是并没有做出什么大刀阔斧的改编。这本该是这部作品的一个优点,但我小瞧了您在表演方面的艺术追求,您这台戏的表演方法真是叫人瞠目结舌,或者称其为“表演方法”是有些勉强的,至少不能算是话剧的表演方法,倒更接近于分角色朗读,而且是角色经常错位的那种朗读,叫人搞不清演员们究竟是否在扮演他们的角色,还是索性彻底忘却了自己的这个基本任务。
但我笃定,您应该是从交响乐或歌剧中得了什么启发,自认为这样的处理手法是有音乐性的妙处,您还给您的演员分了声部,让他们的朗读有了咏叹和宣叙的区分,您挑出了一些语句让他们重复着说来说去,集体喧嚣堪比大合唱。可您为什么偏要挑出那些没什么意味的句子呢?这样的句子再被重复一千万遍也无法生成新的意义吧,只是让我因为感觉到了无意义的拖沓而如坐针毡。
或许您认为,您所采取的这种处理手法是高级且艺术的。我对此十分同意,而且这样的手法对观众而言本不陌生,有很多成功的作品可以作为例证,比如迈克·弗雷恩的剧作《民主》,还有去年借由高清戏剧影像形式引入国内的《雷曼兄弟三部曲》,演员都是在角色内外跳进跳出,时常兼任旁白叙事的任务。但是这些作品的成功有一个前提,就是对演员的表演必须提出更高的要求。

《雷曼兄弟三部曲》剧照
您可以看一看《雷曼兄弟三部曲》,三个演员演了几十个角色,每一次跳进跳出,他们都是用细腻的表演、准确的肢体语言和生动的台词功力,塑造一个新的角色。他们的语气是丰富而多变的,因此无论是他们塑造的哪个角色,男女老幼,角色的灵魂栩栩如生地浮现了出来。又或者他们在以叙事者的身份讲述情节的时候,是真正面向观众娓娓道来的,每一次停顿和转折都用悬念抓住了观众。
反观您剧中的演员,每个人都好像是能够自动行走的朗读机器,依照严密的程序机械地背诵着一段段课文。您的演员们甚至连声情并茂都无法做到,他们的语调如僵尸一般冰冷而生硬,逻辑重音还屡屡违背常理。我不禁想问,您究竟有没有在排练场上花些心思去调教表演呢?还是您坚信为了您所谓纯粹的戏剧艺术就理应如此?那该是对戏剧艺术多么纯粹的误解。
鲁迅的鲁镇还是柔石的芙蓉镇?
如果我说您并没有善待小说《二月》的原著文本,您可能会觉得委屈。因为我注意到您在演出前夕接受媒体采访时特地提到,“要想诠释好这部作品,不仅要读懂柔石,还要全面了解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国近现代文学,就连非常青睐柔石的鲁迅也要多了解一些。”对此我特别同意。但是,是否真的全面了解了文学史和鲁迅,就意味着您读懂了柔石,我想这可能是两码事。
我们能否脱离开鲁迅去谈论柔石?这可能应该算作文学史研究者的功课,而不该由一位戏剧导演来作答,但这确实是我在看戏过程中脑海里不断浮现出来的问题,因为我在舞台上看到了满满的属于鲁迅的符号,比如这铁皮的舞台,还有演员没来由地吼出来的那一句“赵家的狗又叫了”,以至于我不由不生出另外的疑问:被您拿来端放在舞台上的,究竟是柔石的芙蓉镇,还是鲁迅笔下的鲁镇?

柔石 《二月》
我之所以提出这样的疑问,是因为我认为倘若您真的对文学史做了充分了解,理应分辨得出来鲁镇和芙蓉镇是有着时间的区隔的,而这区隔的标志便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具体到这两个浙东水乡的舆情差别,鲁镇上的人们多是惯于道听途说的贩夫走卒,而芙蓉镇的青年进步了,成了习惯读报和口吐洋文的文明人,流言蜚语到了芙蓉镇,总像是无形的瘟疫一般弥漫在通透的空气之中,才更令人苦痛。
可您偏要让这无形的瘟疫显现出具体的形状,于是便从鲁镇抓来了十个衣衫不整的氓众,强塞进芙蓉镇里去捕风捉影。您抓来的这些人可真是歹毒得很啊,他们专门趴在寡妇门前去探听些私密的话,连孩子的无忌童言也不放过,又阴阳怪气地非要生出些龌龊的想法,败坏这至少表面看来还是飘荡着《月光曲》和各种主义的风气,成了这整台喧嚣中真正令人厌恶的反派。
可是,这真的是柔石写下《二月》的本意吗?他真的只是想要揪出几个爱传闲话的闲杂人等来批判?把文嫂逼得自杀,又把萧涧秋挤到女佛山去的究竟是什么?还是您硬要我等观众坐在台下从这90年前的群鬼身上“照见自己的姿态”?如果这就是您独到的艺术读解,那么您的这番读解似乎不仅背叛了原著,恐怕也背离了公论和常理,更算不上高妙,反而是把原著的故事彻底庸俗化了。
没有当代表达的作品岂能关乎“未来”?
观看您改编的《二月》,我其实一直有个十分介意的事情,就是您把小说中最多被提及的女孩采莲虚无成了众角色口中的一个符号。曾有文学界的学者分析说,萧涧秋真正深爱着的并非陶岚,而是采莲。这样的论调虽然有些惊世骇俗,但也可以说明采莲在整个故事中并非可有可无的。对于我来说,她是和陶岚、文嫂并立的第三个女性角色,而且她带给人们的总是关乎未来的一些期望。

您把采莲剥离了出去,人物关系便彻底成了“一男二女”的结构。简单的结构倒是也有简单的好处,二元对立更明显了,陶岚(知识女性)—文嫂(乡下寡妇),两个女性同病相怜,待到无路可走,一个自杀,另一个便挽着她的手走向大雪深处。这是一曲关于女性悲剧命运之必然性的哀歌吗?那么我又搞不懂了,这曲哀歌和当下人们的痛点有什么联系?它和我们今天的社会议题有什么连接?
我们终于回到了当我给您提笔写信时的那些疑问:您真的把这部小说当成是当代作品来创作的吗?那关乎当下和未来的表达究竟藏在哪里了?当您想起过去的时候,有没有思考过,究竟是什么让“未来”进行得不那么顺利了?哪怕,您能够以一些稍微新鲜的观点或眼光来阐明原著中悲剧的真相呢,比如救赎者的无力感,或者人类普遍命运的孤独感,又或者人道主义在私人领域的失效。
但当我看到全剧的结尾处,我发现您的创作意识恐怕已经彻底错乱了,以至于连舞台上的象征概念都被混淆了。您让满台的恶人都披上了修士的僧袍;您让发誓“不再研究音乐”的萧涧秋又弹了漫长的一曲;您让想要追随着萧涧秋到上海去的陶岚披上内衬猩红的长袍,还让您精心布置的深渊泛起了红光。您到底想让我们如何理解这些不知所谓的心机?
我最后想告诉您的是,在我看来艺术创作追求标新立异,标新立异难免有失败风险,但一两次的失败其实本无所谓,端正创作理念,找到失败根源才是重要的事情。一个艺术家不拿艺术当回事,那么他便不成其为艺术家,但是一个艺术家太拿艺术当回事,很可能就陷入了自以为是的魔障之中。这番话确实不那么中听,还请您斟酌。